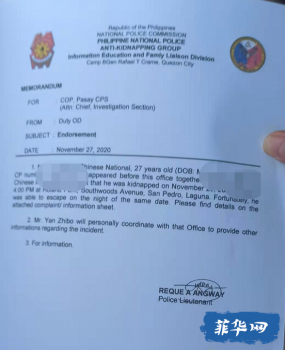(一)全面
这一阵子研讨词牌常见字眼,做了一连串的比较工作,证实牌目有“令”字的多数是短调;见“近”字,属中调天下;“慢”字出头,则压倒性归长调;各领各的风骚。
本文轮到“引”字现身说法了。这个字跟开头第一篇的“子”字一样,在短丶中丶长三类词牌之间平均分布。换句话说,两个都比较普遍化,也可以说全面性。
这一系列先讨论“子”字,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丶在众多常见字眼里面,要数它的常见度最高了。比较一下看:“子”与“令”最常见;“慢”丶“引”次之;“醉”丶“近”又次之。为了避免“教条式酸味”之讥,今後除非绝对需要,不再开列出数目字。想知道究竟有多少支的看官,请自己弄一部词谱来计算一下,还要记得谱与谱之间也常有出入。
“曲”丶“词”……这些字也一样常见,为什麽偏偏看上一个“子”字呢?其中有个缘故,还须费一番功夫才讲得清。常见归常见,却还要分轻重,举个例说明:现在天下第一大新闻是“新型冠状病毒”,简称“新冠”。假设有那位词学大师谱出一支新牌子,取名《新冠曲》,那是理所当然,谁也不会觉得奇怪,因为唐丶宋以来诗丶词丶曲就本是一家,元代甚至乾脆就把诗词叫《元曲》,对不对?但反过来说,如果取名《新冠子》,那个“子”字就难免令人驰思遐想了。还不单如此,放眼“子”字词牌,除了《醉公子》丶《朝天子》丶《安公子》少数几支,删掉“子”字以後,变成《醉公》丶《朝天》丶《安公》,有点不伦不类之外,试看其他的:《渔歌丶天仙丶江城丶更漏丶南乡丶卜算……》
有没有“子”有什麽差别?还不是一样意思吗?!引伸触类,自己不禁要暗问:“牌名用‘曲’丶‘词’来标明是曲调和词牌,可以理解;但‘子’呢?难道词牌还分父子夫妻不成?为什麽硬是要把这个‘子’字塞进去?”这才是优先探讨它的第二个原因。
经过仔细考据分析,“子”字牌除了平均分布在短丶中丶长调三类,相当全面之外,再也找不出任何具有其他作用的迹象,只能下结论:唐丶宋两代的人取名,对“子”字似乎特别锺爱,所以才会有吴道子,而词牌不管需不需要,也放个“子”摆摆样才高兴!
(二)特点
全面性它是像“子”字牌了,但“引”字牌却还具有一些其他的特点。
“引”字牌里面,常见同一支牌名,却出现不同字数版本的现象。这一点酷似“令”字牌,但常见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,多到足够进一步讨论。
讨论之前,先回头温习《小令·短词·殿後》一文,醺老儿提到:“学术研究证明,碰到这种情形(一支牌名多样版本),通常先有短调,然後再产生长的版本……”现在补充一点:长版产生过程,还分成偷懒和创新两种方式。“子”字牌《何满子》原调37字,後来不知哪一个天才,居然一成不变“再来一次”,凑出74字,分成上丶下两片,美其名为“双调”!“令”字牌《如梦令》原调33字,也这样“变”出66字的“双调”来!《梁州令》由52字到104字……这些都是偷懒式加长法的典型例子。
“引”字牌不但有偷懒式,也有创新式,洋洋大观。举几个例子:
无名氏有很多阕《导引》的范词,原调50字,分上丶下两片。他老兄兴致之所至,意犹未足,竟将上下片合为一片,依样葫芦再来个“下片”,倍翻出100字的“双调”!他老兄好像迷上《导引》这支牌,文献中这个牌子,不分单双,悉数由他一手包办。
《梅花引》的情形完全相似:原调57字;双调114字;不过主要作者却换成贺铸。无名氏还填过双调插上一脚,真是物以类聚!老贺昵称原调为“小梅花”,可见投入程度。
再看另一支牌子《迷仙引》(牌名多麽“引”人入胜),有83字和122字两个版本,都是柳耆卿的手笔,前者纯粹属中调格式,後者也十足长调范型,循规蹈矩,不见胡乱缝合重复加倍的破绽。出招想拉长词牌,要像这样,才不枉写作人的本色和创意。难怪後世对历代词家的评价,贺方回始终不如柳屯田;至於无名氏这古板大师,连祖宗的尊姓和自己的雅号也不敢亮出来,就更不用提了。
《东坡引》也有48字和59字的版本,有趣的是:
一丶苏学士本身从未填过这支牌子。
二丶迥异於李谪仙是杜工部两首《梦李白》的主角,苏学士非但不是《东坡引》的主角丶配角丶临场……,竟连一丁点儿的边也沾不上,这才是怪事中的怪事。
(三)平和
“押尾”时,“令”字导致原牌发生字数变化,可能增多,也可能减少。“引”字则夥同“慢”丶“近”字,一律引起字数的添加。举新作与逸峰兄和玉为例:
《千秋岁·饮食诗酒》/ 醺人
饮求对手。食务须宜酒。互交衬,同持久。
茅台汾曲艾,羌蒜芫葱韭。膏扒柳,加餐佐膳咸延寿。
赞李仙诗秀。樽尽毫飞就。逸凡俗,超虀臼。
後生循例干,结雅朋骚友。醺授受,唱和不倦频繁奏!
返步奉和《千秋岁·饮食诗酒》/ 逸峰
精诚合奏。酬唱倾衷受。通灵性,知音友。
达观和韵美,完善循窠臼。篇章就,从容展现辉煌秀。
拓胸期增寿。庭宴邀垂柳。帝王馔,家乡韭。
举杯宣盛谊,丝竹谐声久。葡萄酒,热情敦敬真歌手。
这阕《千秋岁》本来71字,由“引”字来“押尾”,摇身一变成《千秋岁引》,增加到82字(钦定正格。参考书并未注明由谁“钦定”,姑且听信之);几天前拙作《千秋岁引·仲春感怀》是87字的“变格”,又承蒙逸峰兄丶老顽童各惠赐“返步”丶“上步”和玉,已经先後在《南瀛网页》贴出丶《大众论坛》刊登过。限於篇幅,就不再浪费宝贵的喝酒时间,重抄一次了,省得抄的人吃力,看的也够辛苦!
特别提到《千秋岁》和《千秋岁引》,只想讨论一件事:由71到82,甚至87,增加十多字而已。再看《临江仙》58字丶《临江仙引》74字,多出的数目,依然在十来字左右,不像“慢”和“近”字,动辄带来二十几丶三十多字的鼓胀,力道十足。
最後另外比较一下:《婆罗门引》76字丶《婆罗门令》86字;“引”又不如“令”。
所以说:“引”字押尾,虽然具有酵母素作用,却只属於平和的一类。正是:
打气添词皆特异
增光引字最平和
{bbs_source}